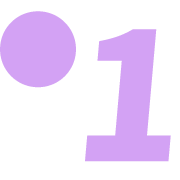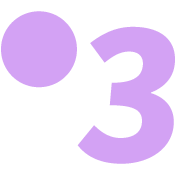爲殺夫女性和失地女性辯護的40年
徐維華已經不間斷地爲婦女權益工作了超過 40 年。
免責聲明:為了便於閱讀,本站編輯在不違背原文含義的前提下對內容進行了適當修改。特此聲明,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站僅作為資訊展示平臺,旨在幫助讀者更全面地瞭解歷史真相。
我們新開啟了更專業的知史明智 PRO 版本(免費),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移步https://pro.realhist.org/,如果對您有幫助請收藏並幫忙推薦,謝謝!
徐維華已經不間斷地爲婦女權益工作了超過40年。
她今年75歲。退休之後,依然在工作,一年到頭各地出差。採訪前她還在山東見幾位失去土地的農村女性,現在她的工作精力集中在遭受家暴的女性。
家暴、失地,這是當前女性權益問題裏,發生最多、最焦灼和複雜的兩種情況。
在媒體的報道中,徐維華常被稱爲“爲殺夫女性辯護的人”。如今我們多數人認同家暴不是家庭內部的私事。然而這個觀點成爲常識,不過是近十年的事。2015年,我國出臺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次年3月生效。在這部法律出現之前的30多年,婦女權益工作者以一種肉搏的決心和姿態,在一線爲受家暴女性奔走。這其中,有一種特殊又極端的情況:女性反殺家暴的丈夫。
談起30多年前的案子和當事人,徐維華有着驚人的記憶力,往事的細節歷歷在目。當時的家暴沒有獨立的法律定義,民間對丈夫打妻子的態度也是默認的家庭糾紛,不少在家暴中被逼到反殺丈夫的女性,都被判了死刑。想起當年沒能打贏的案子,那些沒能救下反殺家暴丈夫的女性,她難掩苦澀、不甘,重複地說“我忘不掉”“接受不了”,這股憤怒持續太多年,成爲她堅持爲受家暴女性代理的動力。
農村婚內女性的另一種處境是失去土地。宅基地,指農村集體組織分配給成員,用來造住宅及其附屬設施的集體土地。村裏分給每戶人家一塊地,用來造房子,而每戶人家通常會分給家裏的每個孩子,然而經常會遇到的狀況是,出嫁的女性會喪失分地的資格,出嫁到其他村的女性甚至會被認爲不再屬於這個村子。於是當離異的女性、喪偶的女性要回到家裏,就會發現,自己已經失去了土地,回不去了。在千千律師事務所受理的3000多起農村女性土地權益投訴中,勝訴的僅佔一成。
2010年開始,徐維華開始接觸失地女性的訴訟。她發現女性遇到的問題會疊加。比如女性受到家暴,同時她是一個農村出嫁女,因爲在本村失去宅基地,考慮到離婚後她無處可去,她難以一下子就離開家暴的丈夫,容易陷入受虐的循環中。
徐維華對我說出的個人經歷,是一代女性如何完成自我教育,又如何施以援手的故事,也是30多年中國女性爭取權利的歷史一角。
文|老衲
編輯|oi
15件
——“於心不忍,冤得要命”
從90年代開始,反家暴就是徐維華的工作重心,其中她經手的重大“被家暴反殺案”約有15件。
1998年,徐維華在全國婦聯維權處擔任處長,有一天她接到一通電話,電話那頭說河北發生了一樁丈夫強暴妻子,妻子殺丈夫的案子。
被殺的男人是一個富二代,賭徒。半夜賭錢輸了,就讓對方去自己家裏強姦新婚的妻子,以此抵賭債。
前面兩次,女人在熟睡中,誤以爲和自己發生關係的是丈夫,到第三次,女人突然開燈,爬上自己牀的陌生男人,翻到牀下,跪在地上求饒,說這是她丈夫同意的。隔日,她準備了一把剪刀放在枕頭下面。
第四次,半夜回家爬上牀的是她丈夫。丈夫要跟她發生關係,她在反抗中,從枕頭下摸出了剪刀,劃破了他的動脈,男人因失血過多而死。
徐維華覺得這不是單純的刑事案件。她是殺夫案的嫌疑人,也是強姦案、婚內家暴案的受害者。“如果撇開強姦案,單獨審理殺夫案,就無法查明事實真相,更加不能適用死刑。”
當時的法律環境是這樣的。《刑法》裏將家庭暴力作爲“虐待罪”規定,《婦女權益保障法》沒有對家暴的定義。案子一審判故意殺人,後果嚴重,影響惡劣,死刑。
“我們覺得理所當然要救救這個人。”
徐維華接到女人的家屬的求助信和案件材料,轉給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她認爲:“死刑要最高法院覈准,本着保護婦女合法人身權利的目的,分清她“以暴制暴”,是在其夫首先同意他人強姦自己妻子,他的行爲事實上構成與他人共同強姦妻子的犯罪。根據案件實際情況,最高法院應當會認真對待,一定不會輕易覈准對女孩的死刑。”
徐維華希望不判處死刑。最高法刑庭的庭長答應她會慎重決定死刑。等到徐維華去外地參加外會議回來,不過一週的時間,她得到的消息是,女人已被執行死刑。
沒辦法挽回生命,刀下留人失敗,徐維華一直對此耿耿於懷到現在。每每提起,說的都是“她受盡侮辱”,“忘不掉,不可以接受,不能接受。”“於心不忍,冤得要命”。
136人
——“這個意識不是天上掉下來,不是地上長出來的”
這樁案子加速了徐維華的提前退休。54歲,她決定離開全國婦聯,加入反家暴網絡。千禧年交界,女性思潮湧動之時,反家暴網絡一度名聲顯赫,集合了一批學者和ngo工作者,做教育的,法律的,從醫學角度分析家暴的,從事農村婦女權益研究的。
徐維華在高考恢復前夕,1977年被推薦上了大學,學法律,畢業後被分配到杭州大學教書。1983年她進入全國婦聯法律顧問處。當時她只是本能地覺得用法律維護婦女權益是個很好的事情。在婦聯工作時她獲得了律師證書。
在那個年代,爲性別平等努力的女性,大多數是城市中的精英女性,她們看到了不同女性羣體的痛苦,想要做點什麼,但她們能獲得的資源並不多。缺少國際交流、沒有互聯網、資金支持匱乏、性別理論研究還未普及。
反家暴網絡培育和影響了幾代婦女權利工作者,如今活躍的女性權益組織的創始人和核心成員,許多都曾和反家暴網絡有或緊或密的聯繫。
2012年,徐維華關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正式加入千千律師事務所,以律師身份介入反家暴個案,爲弱勢的,無力支付高額律師費用的女性維權。
2013年,徐維華和千千律所的創始人,她從80年在婦聯就認識的好友郭建梅,在四川的看守所見到了李彥。
李彥一審被判故意殺人罪,死刑立即執行。眼前這一位戴着手銬腳銬的死囚犯,也是一個殺夫的女性。
李彥和她們講了婚後遭受的家暴,以及婚內強姦、性虐待。
李彥和譚勇都是再婚,李彥有一段婚史,有一個女兒,譚勇有三段婚史,有一個兒子。鄰居說譚勇以前的老婆都是被他打跑的,但他對李彥承諾“以前我的脾氣是暴躁,說不到兩句話就打人,現在我一定改”。
婚後,他很快露出了婚前隱藏的暴戾脾氣。遇到一點小事就罵她,李彥還口就會被打。每個月都要被譚勇打幾次,打得鼻子嘴巴都是血,扯她的頭髮,按住她的頭往牆上撞。毆打完強迫她發生關係,甚至在她做完刮宮手術的當晚也被強迫發生性關係。用菸頭燙她,白天對外讓她謊稱做菜被油燙傷。有時把她趕到陽臺上,不許睡覺。限制她的行動,比如不能回孃家,不能出去幹活。
李彥不是沒有想過逃的。
她提出過離婚,商量好離婚後財產和債務分配,對方不同意,要求若離婚財產全部歸他,債務全部歸李彥。協議未果,提離婚成爲了新一輪暴力和威脅的開始。她也不是沒想過求助。婦聯、社區,報過警。派出所讓她找婦聯反映,婦聯讓她找社區幹部和親戚朋友幫忙,社區說害怕譚勇找上門,去找婦聯解決。
有一天凌晨,在他們住的工地小賣部裏,譚勇又喝醉了,拿着氣槍說:“不打你腦殼,打你屁股,看打不打得穿。”他一腳踢在她大腿上。在爭執中,她拿起架在牀邊的火藥槍管,砸向譚勇的後腦勺。隨後她又打了一下。血冒出來,他倒在牀上,死了。
隨後她分了屍。第二天她把裝在編織袋和塑料袋裏的屍塊丟到廁所、河裏。
法庭上,李彥向法院提供安嶽縣中醫院2010年8月4日診斷證明,其左腿、胸部多處受傷。還有自己去照相館拍的傷口的兩張,照片裏她的頭部、頸部受傷。安嶽縣婦聯的接待記錄,顯示李彥投訴再婚後多次遭譚勇毆打。安嶽縣外南街派出所的接警記錄,稱李彥反映當晚遭譚勇毆打,“譚勇經常打她,有家庭暴力”。李彥提供給警方的日記中,多處記載被譚勇打罵的情節。
可是,法院認爲這隻能證明她受過傷,而無法證明傷害來自譚勇。她對社區、派出所和婦聯反映過情況,但只有她一方的說辭,沒有譚勇家暴情況的核實和他的說辭,家庭暴力的證據不足。法院的判決認爲她不是因爲“家庭暴力”殺人,而是“家庭糾紛”殺人。徐維華常常說,基層的從業人員也應該有女性權利的意識。在事態尚未到最嚴重的時候,是有機會干預的。可是傳統的觀念,阻礙了他們對李彥所面臨的處境的認識。“這個意識不是天上掉下來,不是地上長出來,是靠不斷地呼籲,以及不懈地學習。”
重審的庭審現場,徐維華讓李彥舉起她的左手。
李彥曾得知譚勇有婚外情。當她和譚勇及情人對峙完,譚勇問她,剛纔用哪個手指着那個女人?李彥伸出左手中指。譚勇操起斧頭,手起刀落,左手瞬間血肉模糊,她的中指被切斷一節。
徐維華讓李彥別放下,所有人都看到了少了一節的左手中指,還有比這更直觀的痛苦嗎?
在法庭之外, 正值《反家暴法》立法階段,這起案件引發了廣泛關注,也影響了法律的制定。有136人簽名的緊急呼籲信希望刀下留人,信中寫道:這是社會和法律缺乏家庭暴力對弱者有效救濟途徑的悲劇。終審判決結果是認定家庭暴力,死刑緩期執行。
30年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懲罰這個男的”
這幾年徐維華經手的嚴重反家暴案件明顯變少了。“《反家暴法》施行,以及社會對家庭暴力的認識不斷深入,極端的家庭暴力案件在我們這裏求助的不多了。現在很多家暴案和這個時代的變化有關,比如離婚過程中,隨着感情破裂,出現了家庭暴力。”
有一個女孩來找她,個兒很高,人也漂亮,工作體面,她網戀認識了一個男人,見了一兩次面,背景都還沒了解清楚,就閃婚了。婚後沒幾個月,對方在她的微信朋友圈裏找她的朋友同學,編造橋段來騙錢。他在婚戀網站上寫自己是碩士,其實初中有沒有畢業都是問題。他稱自己沒有婚史,其實結過三次婚有孩子。
當她發現真相後想要離婚,男人不同意。只要她還想離婚,男的就不允許她回單位上班工作。將她身上所有的錢和十幾個名牌包都被拿走,加起來幾十萬,用於工作的職業證明被藏匿(銷燬),最後她被強制關在家中。他手裏有管制刀具,還有手銬等器具,不停地打罵她,恐嚇她,情緒到了崩潰的邊緣。
女孩終於找了一個機會,逃出來了。爲了一紙離婚協議,女孩花了很大的力氣。警察接了報案,但是以沒有證據,也沒有錄音錄像爲由,偵查工作停留不前,事實上她在經受嚴重人身安全恐嚇、威脅的時候,她無法拍到什麼照片。
“在私密環境裏,怎麼取得證據?”後來她無奈在抖音上實名舉報,徐維華委託代理後去調資料,希望加大偵查力度。徐維華想了很多辦法,發現只能先上訴離婚,不然她沒有任何別的方式可以把婚離掉。“離婚是要保護她,除此之外,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懲罰這個男的,這是無奈的。”
如果說30年前,在缺乏法律約束和社會認知的情況下,家暴以各種隱祕的形式存在。30年後,家暴沒有消失,它以新的方式存在。徐維華希望不要到以暴制暴的時刻,我們才意識到要伸出手。
3000多起
——“這樣一來,她們要去哪裏呢”
2000年初開始,千千律所接到全國各地的失地女性的電話。徐維華的同事、千千律所農村婦女土地權益項目負責人林麗霞估算過:“這20年來,律所受理的3000多起農村女性土地權益投訴,勝訴的佔一成,更多是敗訴或法院不受理。”
通俗一點來說,那些失地的農村出嫁女被排除在村集體之外,分不到本村的宅基地、拆遷補償款,哪怕是婚前有地,婚後也會被收走。至於爲什麼她們被排除在外,多是基於“村規民約”。在傳統的婚嫁習俗裏,女性婚後從夫居,參與夫家的利益分配,在本村就是“外人”。但這條默認的規定,沒有考慮離婚的女性、單身的女性,以及招了贅婿的女性。
徐維華從2010年開始接觸出嫁女土地權益問題。她記得一個現在講起來都要咬牙切齒的案子。十年前,在湖北的一個村子裏,大量出嫁女的土地權利被奪走,她們用各種辦法來申訴自己的權益。
徐維華和同事在湖北爲出嫁女爭取權益
村長原本是一個殺豬戶,他對出嫁女的訴求不予理睬,說上面的領導都認爲不能給她們。徐維華她們跟村幹部溝通,希望他們意識到保護出嫁女權益是村幹部的責任。她跟他們普及《婦女權益保障法》,女性和男性村民享有一樣的權利。說一千道一萬,對方只回:“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她們再也不是村裏的村民。”
“她們的戶籍在村裏,她們從出生到現在一直生活在村裏,是誰不讓他們成爲村民?她們在不久前接到村委會發給她們的選舉證,你們在需要選票的時候,將她們作爲村民去給你們投票,剛剛投票結束不久,使用完了,她們就不是村民了?用這種手段剝奪她們對土地的經營承包權利,太卑鄙了。這不是出嫁女不享有土地經營承包權,而是,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權利和利益的掠奪、侵佔,村委會成爲掠奪者的撐腰工具。“
最後村長說,既然她們說村規民約違憲,她們去告,那他就組織村民公投,他們村委會和村民代表大會通不過。
“我們去做這些工作的時候,真是求爺爺告奶奶,他們講什麼村規民約,理直氣壯的。一點辦法也沒有。我當時就特別生氣,你們做了工作嗎?村代表大會投票的大多數是男性,你好意思說投票,他們怎麼會希望有出嫁女來分自己的土地?”
她發現這十幾年來,來找她們維權的女性,年齡層越來越往上,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女性,她們的困境很深。採訪之前的幾天,她剛剛在山東見了兩位離婚的中年失地女性。
“現在我們會遇到離婚的老年女性。結婚30、40多年,如果她沒有經濟能力在外面有個房子住,那很大可能是繼續隨前夫居。她的生產、生活得不到保障,如果有的婦女因遭受家暴導致的離婚,因住房不能離開,很可能離婚後繼續遭受暴力,還不能排除會不會遭受前夫的性侵與性騷擾。受到限制的還有她的工作勞動權利,她的獨立性、隱私權都得不到實現。結婚那麼多年,她的孩子都有孩子了,她怎麼回孃家?孃家已物是人非,如果父母不在,兄弟分別成家立業,你讓她的哥哥還是弟弟接到他們家住嗎?屬於她的塊是哪地?屬於她的家又在何方?她再也回不到這個生她養她的地方。類似這樣的女性活生生地存在着,確是有名有姓的人。”
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失地女性爲了解決自己的生存,至少有個住的地方,她就得被迫選擇下一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女性20歲左右,正是年輕能幹的時候,在兩性市場上有優勢。到這個年紀,她被認爲不再有生育功能,經濟能力又衰減,在婚戀市場上是沒有太多話語權的,已經沒有太多選擇男性的空間。徐維華知道有兩個中老年出嫁女,由於土地權問題得不到解決,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嫁人,已經先後結婚7—8次了。
“這樣的案例太多了,還有一些情況,第二段的婚姻實在忍受不下去,離婚,再選擇第三段,越往下選擇,越悲慘。出嫁女的事情,一提起來我就要淚目。”
那選擇不再結婚的女性呢?她們留在夫家村,要從已經解除婚姻關係的男方的村集體中,爭取她們的權利,可以想見是怎麼艱難的處境。“有些村民對她們極盡歧視和排擠,侵犯她們的權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離婚女性本來已經在經受人生中的低谷,打擊,有些還帶着孩子,生活可想而知,生活狀態和質量嚴重下降。她們的土地權益是被侵害、被剝奪,可見她們中許多人悲慘的命運。”
2024,第一部
——“幾個女人能翻出什麼浪來”
2024年6月,經過三次審議,我國第一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通過,將於明年5月1日施行。立法過程裏,爲失地女性奔走的律師多次提議,希望將出嫁女、離異女性、喪偶女性納入集體成員資格,有資格獲得屬於自己的宅基地,土地被徵用後分到徵地補償款,參與村集體的利益分配比如分紅。多數立法建議被採納,不過村集體成員資格認定,依然是交給成員大會表決。
許多女性沒有收入來源,支付不起律師費,徐維華她們免費提供法律援助,還自己貼差旅費。
她說自己沒有畫畫的天賦,沒有唱歌的能力,好像這輩子只會做婦女工作。她沒有任何要停止工作的意思。得知某個素不相識的女人遭遇的痛苦,她依然會“氣得跳腳”“忍耐不下去”“無比憤慨”,大罵施害者“思想心靈醜陋不堪”。
“還有這樣的問題存在,就是說社會還需要我這方面的能力,我提供一點幫助,對個人來說能幫到她們一點,對受傷害、受委屈、受苦難的女性盡點微薄之力,也能紓解從事多年婦女權益工作,但得知還有這樣的女性存在時,心裏面的無比愧疚。我不是權益受侵害女性的救星,也不是救命稻草,但能幫一點是一點。我的命運與婦女結下了不解之緣,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我願意一直做下去。”
“去村裏維權的時候,有人說幾個女人能翻出什麼浪來。我想讓他們看看,我們能掀起什麼樣的巨浪。”
(文中配圖均來自受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