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救不了年輕人
免責聲明:為了便於閱讀,本站編輯在不違背原文含義的前提下對內容進行了適當修改。特此聲明,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站僅作為資訊展示平臺,旨在幫助讀者更全面地瞭解歷史真相。
我們新開啟了更專業的知史明智PRO版本(免費),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移步https://pro.histfacts.com/,如果對您有幫助請收藏並幫忙推薦,謝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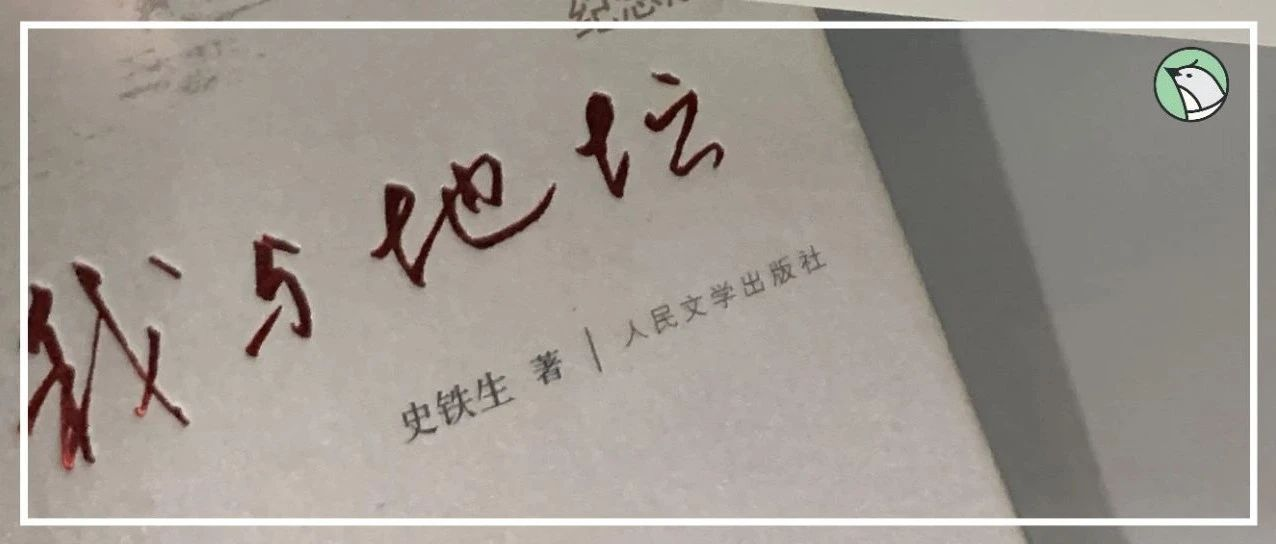
作者|廖宇彬
編輯 |江臾
出品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可這文筆,
也不是史鐵生的啊?”
餘帆是在史鐵生的文字裏找到流量密碼的。
他是電子商務專業的大二學生,兼職短視頻平臺的博主。賬號起源於電商實戰比賽,他原本做大學生生活,但視頻拍攝策劃難度太高,數據一般。
轉型讀書博主是最效率的選擇。一句深刻的話,一個有設計感的背景,配上一段恰當的配樂,一個五秒的視頻誕生。在無數名人名言中,餘帆發現史鐵生格外受用戶青睞,視頻封面打上“史鐵生老師也太會寫了!!!”保準小火一下,“流量會說話。”
他第一次嚐到甜頭便是網上刷到的史鐵生語錄,原文是“史鐵生說:不要急,死亡一直在等着你。好像死亡是一個你非常討厭的結婚對象。那麼好的,既然必須和這個無聊的傢伙結婚,我一定要把我的忠貞,我的熱情,我的好奇心,我的愛浪費在這個世界上,把一副空殼留給死亡。”餘帆只看見和搬運最後一句,發佈後,當晚流量躥上百萬+,漲粉千餘,餘帆登上後臺時,幾乎控制不住微微發顫的指尖, “火了!”
這是一場互動狂歡。餘帆整晚都沉浸在迅猛增長的評論區欣賞,發言分爲三類,一類感嘆史鐵生好會寫,如“病隙碎筆超級好看,每讀一篇都會被史鐵生的思考震撼”;一類抒發感想“死氣沉沉的我突然想熱烈地活着了”;第三類最多,搬運史鐵生的其他金句,譬如“愛是自卑棄暗投明的時刻”,或單純把視頻原句複述一遍,這些評論點贊都能輕鬆過萬。
一條讀書博主的康莊大道似乎鋪在眼前。直到第二天,有人指出,這不是史鐵生的原句。
餘帆心如擂鼓,他去網頁考證,“真錯了”,原文出自餘秀華的《無端歡喜》,只是對史鐵生的評論,一整段只有第一句是原話,“史鐵生說:不要急,死亡一直在等着你。”
也有神奇的事。在搜索界面,餘帆仍然看見衆多官方媒體、大V甚至外網threads在引用這句史鐵生語錄,文章標題各顯神通,“全網嘴替史鐵生,把00後的集體痛苦說透了”“永遠被史鐵生的文字所震撼”“14年後纔讀懂史鐵生的頂級文筆”。
“可這文筆,也不是史鐵生的啊?”
當天餘帆迅速在評論區發佈道歉和勘誤,但視頻不斷湧來新的用戶,這小段文字迅速被新評論淹沒,他只能截圖這段道歉,重新置頂。即便如此,據餘帆觀察,用戶們重複着以上三類評論,勘誤的點贊只停留在一千餘,至於質疑的人,不過幾十贊,他有些失落,“不是每個人都會注意或者在意,對吧?”
烏龍過後,餘帆買回《我與地壇》(下文簡稱《地壇》)和《病隙碎筆》, “我會認真讀原著,再繼續分享史鐵生的。”
餘帆買回《我與地壇》©餘帆
史鐵生不會想到,在他去世十四年後,他會被新一代的年輕人推至王座,成爲“一句話治好精神內耗”的文學導師。讀史鐵生已經成爲一種新潮流,無論互聯網哪個平臺,你都能發現海量“史鐵生頂級文筆”“《地壇》來北京一定要做的事”等內容。根據視頻平臺所發佈的《2024抖音讀書生態數據報告》,史鐵生相關的視頻累積達18.6萬個,視頻總時長增長415%,《地壇》也成爲最受歡迎的名著。
“秋天帶本鐵生的書去地壇走走”已經成爲火熱的打卡項目。昭玉在秋天來到地壇,正是銀杏葉落的季節,大道鋪滿金黃落葉,在無數手拿相機的遊客,悠閒遛彎的大媽大爺中,昭玉能精準地辨識出許多“同類”,年輕人,不時看看手機,拿着一本史鐵生的《地壇》,若視線相對,便相視一笑,然後各自低頭拿書拍照,互不打擾。不用猜,定然是爲史鐵生而來的。
©昭玉
專欄作家潘採夫是“史鐵生分享會”的受邀嘉賓之一。今年夏天他也去過地壇,一個工作日早晨,意外地遇到四五張年輕面孔,在晨練的老年人中格外顯眼,即便手中沒拿書,潘採夫的直覺告訴他,這些孩子是來尋蹤的。後來一問一個準,她們都尚未成年,最小的剛上初中,剛讀過《秋天的懷念》,想來地壇走走。
對於2000年後出生的Z世代而言,中學課本里《秋天的懷念》是他們對史鐵生最早的記憶,文中母親的愛意和離去的遺憾十分動人。在潘採夫看來,教材對相關作品的納入,爲史鐵生在年輕人中的影響提供了第一推動力。
昭玉也記得這篇課文,當時的語文老師講到“母親去世”那段時嘆了氣,“等你們長大後再來讀讀他的文章。”這一過便是十多年。
去年6月,她辭職在家,想要做點什麼逃避上班。昭玉在不同的平臺搜索好書推薦,“哪本書能帶給人力量”,無論哪個博主推薦多少本,榜上有名的一定是《地壇》。
爲什麼是《地壇》?
楊柳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她曾負責出版史鐵生的數十本著作。據她觀察,這兩年史鐵生更加火爆,銷量幾乎翻數倍,《地壇》和《務虛筆記》尤其突出,前者與史鐵生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很好讀;後者也許是第一部長篇,知名度高,“也許史鐵生個人的勵志,能讓青年人的緊繃稍稍放鬆吧。”
潘採夫也很理解這個選擇,“好讀啊!”史鐵生公認文學成就最高的書,也是他晚年最後一本《我的丁一之旅》,由於行文晦澀抽象,潘採夫常常一天只能讀一頁,“鐵生晚年身體有限,想得很多寫得很慢,一天最多200多字,所以他要用最少的字數表達最深奧的思考,定是難讀的。但《地壇》在鐵生二十多歲時誕生,多是散文隨筆小說,雅俗共賞。”
程遇喫到了地壇這口紅利,她寫了篇圖文,以“鐵生,我想起你的文字”等對話體排比抒情,標題含有關鍵詞,“地壇”“北京讀大學”,這篇文字迅速過萬贊,“其實我是有意識的,肯定有,否則也不會這麼寫了。” 程遇已經察覺到,“地壇和史鐵生就好像自帶一堆流量。”
程遇的筆記獲贊過萬 ©程遇
很多人給她留言,“下次也要帶《地壇》去地壇看看。”
“你有帶《地壇》去嗎?”我問她,她回答:“沒有,我可能只在筆記裏提到史鐵生和《地壇》,但更多是去逛逛和拍照。公園的樹太好看了。”
“史鐵生像那種999感冒靈,
喫了就管用”
解璽璋是民間史鐵生研究會會長,也是史鐵生的多年好友,但直到被邀請參與“史鐵生分享會”之前,他對“年輕人愛讀史鐵生”這件事都沒有實感。我問他,“您會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呢?”解璽璋也很疑惑,“我特別奇怪啊!他們怎麼就愛看呢!”
史鐵生有着傳奇而坎坷的個人經歷。他1951年出生於北京,活躍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壇,21歲雙腿突然癱瘓,28歲開始文學創作,沒兩年罹患腎病,後來惡化成尿毒症,59歲逝世,他就在方寸輪椅之間完成了數百萬字的創作。
解璽璋推測,“現在的年輕人在情感、精神等方面都遇到很多困境,鐵生作爲一個殘疾人,在《地壇》裏集中他對前20年生活的思考,包括如何走出生命的困境,年輕人能找到一種共鳴吧。”
關於爲什麼要讀史鐵生,每個人的答案更是五花八門,但細究又實在相似。餘帆也給我念了一串史鐵生的生平,經歷如何坎坷,身體如何飽受折磨,但文字又如何深刻,能說出那些他表達不出的想法,簡單來說就是嘴替, “史鐵生理解生命。”
事實上,當你開始思考生命和死亡,不論嚴肅沉重的還是調侃詼諧的,你一定會遇到史鐵生。也許是受困於身體,或有感於時代,史鐵生總在談論死亡,解剖死亡,餘帆記得那句“死是一個必然降臨的節日”,幾乎塑造了他的生死觀。
餘帆曾有過真實的自殺念頭。他在河南讀高中,高一高二在家中上網課,高三恰好在疫情的末尾,寒冬封校四十多天,和外界完全隔絕,餘帆每天只能盯着早五晚十的作息表,上課和作業都沒有盡頭,手要縮一半在衣袖裏,既沒那麼凍又還能寫字。有一天窗外下大雪,餘帆控制不住幻想,要是死了多好,“也是苦中作樂了。”這些回憶斷斷續續,他還有些恍惚,“這居然只是去年的事。”
也是在這段時間,餘帆第一次在互聯網看見史鐵生的文字火起來,讀到那句“太陽落下又是升起”。
幾乎每個人和我聊到《地壇》時都會提到這句話。原文是“但是太陽,他每時每刻都是夕陽也都是旭日。當他熄滅着走下山去收盡蒼涼殘照之際,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燒着爬上山巔佈散烈烈朝暉之時。”
餘帆說這是一種“生生不息”,人不必再對死亡抱有恐懼,它並非終點。
還有一句話,“一個拿死說來說去的人,以我的經驗來看,並不是真的想死,而是在渴望愛。”餘帆讀到這句時恍然大悟,“原來我想死也不是精神不正常,可能是缺愛。”
©餘帆
做賬號後,他經常會看見評論“每次想死,看完史鐵生老師的話覺得還能再活一下”,他頓了頓,說出一個新名詞,“死人微活”。意思很簡單,指生活就在一種淡淡的死感中偶爾迴光返照,配套名詞是“活人微死”和“命縮力”,指人沒那麼想死,但也沒那麼想活。
年輕人似乎又後退了一步。去年流行的發瘋文學,生活還有掀翻桌子向外發瘋的出路,至少人仍然是活的;今年默認主語已死,網絡隨處可見 “人都是要死的,我們都是預製屍體。” 偶爾振奮一下,也只停留在“我的屍體暖暖的”。
儘管只是讓“屍體”暖了一點,但年輕人很需要這種能量。
楊悅特別理解“去史鐵生那裏尋找安慰”這件事。當覺得自己倒黴、日子沒進展的時候,她就讀史鐵生,“他生平多坎坷,一直生病,母親很早去世也沒見到他的振作和成功,人生主觀體驗真的非常差。而且莫名其妙的天降苦難,一種突然好倒黴的感覺。”
書中的鐵生不斷反芻這些痛苦,同時又隱含豁達精神,不論價值觀正確與否,她看完心裏都會好受很多,“特別像那種999感冒靈,喫了就管用”。
楊悅曾是優績主義的勝利者,從小到大成績頂尖,一路都是優秀畢業生,能做科創,也能寫新概念,又考入北京的頂尖大學。在選專業的時候,她放棄了經濟學類,最終選擇了哲學,原因是讀了周國平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在那本書裏,作者精彩地闡釋了尼采晦澀難懂的學說,她也想做到這種傳播,“18歲,更應該追求自己的理想吧?”
不過四年足夠哲學“夢碎”,爲了未來能有口“更好的飯”喫,她輔修轉行經濟學,頂着不對口的專業,一年內從金融小黑工幹到投研實習生,畢業後出國實習,“說實話我已經足夠幸運,甚至可以算一個什麼成功案例,但爲什麼還是這麼痛苦?”
她去參加學校的秋招雙選會,抱着二十多份剛編好的簡歷——那些絞盡腦汁羅列上去的實習和項目,試圖奪取hr對“哲學系”的注視。雙選會在小廣場,她繞着企業的小攤轉了一整圈,國企央企私企大廠,即便相關金融機構,也掛着小牌,“歡迎理工科同學諮詢”,終於看見“文科可投”的出版社,一看海報,“只招4人,最低學歷碩士”。回頭一看,數十人在排隊諮詢。
同班同學也在,他是男生,進入會場就收到一堆傳單,hr們熱情洋溢,“清本啊!好”,“男生啊!好”,一問專業“哲學”,三兩個負責人露出只可意會的微笑,“那可惜了”,她聽見。最後,楊悅沒投出去幾份,給了的多半也“泡池子”。
神話只存在於學長學姐的傳說之中,“19年前的形勢多好,工作多容易拿offer,實習無需卷生卷死,績點沒有這麼高,他們能在週末自由地跨省旅行…… 等一切都結束,大學也要結束了。”
她感覺自己的痛苦甚至沒有靶子——到底該射向哪裏?紅利退去的時代、找不到的工作、日益高中化的大學、沒有退路的人生還是不甘心嵌入齒輪的自己呢?
至於年輕人喜歡史鐵生,她給我從經濟學的角度做了分析,“經濟沒那麼好,對應的就業和社會環境沒那麼有力,人們要找尋價值觀的錨點,從哪裏能獲得安慰呢?你看經濟擴張的時候,人們就會去找很有野心的成功企業家,比如叫馬雲爸爸,那是一種侵略型的價值觀。但現在行不通了,更有效的是內傾、關注自我的觀念,越往下的人陣痛越明顯,但每個人或許都能在史鐵生這裏得到安慰。”
“你想逃離一個地方,
但你發現根本逃不掉”
張升是在讀書軟件聽完《地壇》的。方便快捷,不需要太用腦,也很有感覺——夜深人靜躺在牀上閉眼,腦中就能虛構整個畫面,史鐵生在地壇搖輪椅的背影,隔着時空出現在他眼前。
張升絕對算不上史鐵生迷,他只是一個碰巧遇見史鐵生的人。
有一天失眠,腦子裏亂糟糟,回放去年失敗的生意,他碰巧刷到一段音頻,那渾厚又安定的聲音立刻擊中他,是史鐵生曾經在央視的原聲,念《我與地壇》,“我常覺得這中間有宿命的味道……那時,太陽循着亙古不變的路途正越來越大,也越紅,在滿園瀰漫的沉靜光芒中,一個人更容易看到時間,並看見自己的背影。”讀到最後兩句,張升很激動,“封神了。”這種言語的力量很強,“你就感覺人生總有困境,你也要知道和麪對。”
張升的賬號 ©張升
張升今年22歲,已有6年工作經驗,從職高退學到現在,他戲稱自己“360行都幹過”。
退學是主動的,他對上課沒什麼興趣,反而更投入於課外書,“青春期內心有情感變化,你無法表達出那個東西,也不能跟大人說,只能看書”。那時他喜歡太宰治的《人間失格》和餘華的《活着》,描寫的太慘又太真,但也有困惑的地方,“你說太宰治一個有那麼好文憑的人,爲什麼三次跳河自殺?”
退學後,他曾想去佛山做房地產銷售,因爲常在短視頻刷到,看起來很賺錢,父親制止了他,“未成年人跑過去不怕被騙?”於是他在本地縣城找了個餐館當服務員。滿18後,父親希望他去浙江,至少有親戚的照應,第一份介紹的工作就是進汽車廠,做裝配工。
他最不喜歡的也是進廠,24小時關在流水線車間,他有一種不知往何處逃的煩悶。沒多久他就離開了,他當了騎手,送快遞也送外賣,他告訴我,“很自由”。他喜歡騎着小車在城市街道里來回穿梭的感覺,至少在路上,還能享受免費的微風,和沒有天花板的敞亮感。
但張升仍然時常感到苦悶,又找不到情緒的出口,“節奏太快了,人太浮躁,我有些跟不上。”
送快遞的兩年,大領導要結果,領導要數據,最後壓在他一個基層普通快遞員的身上。從零開始學做ppt,不是那種大廠的彙報文檔,這是他們業內的黑話,指做假數據。上面給的標準如派件數量達不到,張升就要編,還有的公司下發推銷產品的指標,他無法完成,最後自掏腰包補上指標。他很迷惑,還透露出少許的忿然,“這太不真實了,形式也太假了。”
即使肩負這麼多任務,張升的工資只有四千,直到後來幹了兩人份的活,早五晚十,負責幾個區域配送,他能拿一個月一萬多,至今仍津津樂道,只是也沒幹幾個月,“身體累不住了。”
送外賣路上拍的風景 ©張升
他痛苦於努力和回報完全不成正比,我問他,“你覺得這什麼原因?”他想了想,“現代社會的縮影。對於勞動工作者是很普遍的現象。”他又補充,“我們同事很多年輕人,經常會聊這些的。”
苦悶的另一側是孤獨。他在重慶農村長大,父母都是農民,父親酒後訴苦是家常便飯,“這一生值不值得呢?”家人沒有耐心也沒有精力聽他訴苦,現在外出打工,他偶爾接到家裏電話,“累是無法開口的,他們只會覺得你現在這麼好,有什麼過不去的。”
我很好奇,“你後悔過退學嗎?”
“班主任跟我說過,每個人都要爲自己的選擇買單。”
他剛出來做服務員時,有一桌是大學生,路過時他聽見對大學的討論,一種失落夾雜着懊悔的感覺裹住他,“如果我能好好讀書,是不是也能上大學?”但是這縷模糊的懊悔迅速消散在顧客呼喊他的聲音中,後來他也很少再想起,“是接受了。”
出來後,張升確實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一個人上班下班有工資,回家就躺着打遊戲,但一年多過去,獨自回家面對小小的出租屋,一種強烈的孤獨感襲來,張升不知道還能做什麼。他買了七八本書,李銀河梁永生都有,但那些人無法幫助他,“讀了一點也沒意思。”
他也交過女朋友,但“一個人的世界突然出現另一個人,你就會緊緊抓住,然後她又走了。”這麼多年來來去去,張升意識到只有父母會真正在乎你,他需要這種在乎,“你想逃離一個地方,但最後你發現根本逃不掉。”
張升把這些情緒都命名爲“現代人的浮躁”,抑鬱、焦慮和沒有方向感,需要一些正能量來緩衝,他很肯定,“史鐵生就是正能量。”
張升並不喜歡這種生活,“只是接受了。” 他曾經有個深埋的作家和自媒體夢,但比起其他更“腳踏實地”的工作,那個夢太不現實了。
他也投過小說。剛工作後的一年,他無法壓抑表達的慾望,兩三千字的短篇,模仿太宰治寫現實札記,主人公有着他的影子,“羞怯膽小的性格”,後來沒有迴音,他早忘記情節內容,“平平淡淡吧,原稿應該都刪了。” 他還仔細研究過《收穫》的投稿和稿費標準,結論是,養不活自己,再後來, “踏入社會後,雜七雜八的事太多,思緒太多,就再也寫不出什麼東西了。”
現在張升已經很少閱讀一整本小說,聽書是更簡便的方式;他也很愛紀錄片,但更適應短視頻裏的十分鐘解說。但聽到那段史鐵生的音頻時,他非常激動,久違的分享欲迸發,曾經做自媒體的想法死灰復燃。他簡潔剪輯後,搬運到短視頻平臺,當晚數據就爆了,許多人都評論,“雖然第一次聽,但覺得鐵生就該是這個聲音。”
“爲什麼要比較痛苦”
面對這種突如其來的潮流,其實解璽璋很警惕,“話說的不好聽,但他們有點把史鐵生當做心靈雞湯,大概是我們這些人不願看到的。”
“我們這些人”都是曾經的年輕人,熱情昂揚地歷經動盪年代,於大學後讀書沉穩,立志要做到更文學性的閱讀。解璽璋讀史鐵生的起點在《我的遙遠的清平灣》,那是史鐵生的早期作品,記錄他下鄉插隊的故事。解璽璋很喜歡這篇,“沒有通常寫作的兩個毛病,一個是訴苦,覺得自己不幸經歷苦難;另一個是懷抱改造農村的理想,以失敗告終。歸根結底都是過於自戀。”
在他看來,心靈雞湯同樣有自戀的毛病,它就像營養品,是對心靈淺層的撫慰。現在解璽璋已經很少接觸年輕人,但他有一種泛泛的感覺,“他們貌似獨立自主,實則內心脆弱,缺乏一個主心骨——那種真正獨立的主體性和自我認知,獨立思考和判斷。”
但年輕人們也會很快發現,心靈雞湯在很多時刻也是無力的。
楊悅不再相信“xx階段很重要”、“過了xx就好了”這些空頭許諾,她不要過社會時鐘裏“關鍵的一生”,愛咋咋地隨便活着吧,“反正又不會死,再說,真死了又怎樣?這都不是我能決定的。”
她記得第一次讀《好運設計》時,興沖沖地去找母親,硬挑一段念給她聽,“他(史鐵生)在文中說沒有完美人生,我就想我的人生已經很幸福,不該抱怨生活和命運。”她不記得後續,但母親應當是沒什麼興趣的。
今年再讀,她無法按照書中的想法感謝命運。相反,她在《好運設計》和《活着》中感受到一種相似的價值觀,即無論你遭遇什麼苦難,都要活,活着就是爲了活着本身。楊悅不相信這是唯一的答案,“爲什麼活着是最高價值觀?爲什麼要設計苦難才能體會到有成就感的幸福人生?這裏總教我們忍耐痛苦,去發現自己的價值和意義,但很多人在發現之前就已經痛苦死了對吧?”
她想起自己的金融小黑工生活,凌晨一點被帶教喊起來做數據和畫ppt,大腦裏的神經在“翻皮筋”,她的手理智地開始畫,條件反射地勸慰自己,“你看大家都這樣過來的”,麻痹半晌,楊悅突地爆發,“仔細想想還是太他媽難受了”。
再向前一步,她更加困惑,“通過比慘去理解史鐵生是不是本就不對?以他人殘疾的境遇激勵自己是否本身就是一種暴力?爲什麼要比較痛苦?你並不是看到別人比我慘自己就能好受的。”
楊悅接觸文學很早,初中時語文老師就向她們推薦大批著作,史鐵生、畢淑敏、龍應臺構建了她最初的世界。但初高中讀史鐵生很功利,無非是背些名句爲高考作文增光添彩,隨手引用如“且視他人之疑目如盞盞鬼火,大膽地去走你的夜路”,議論文昇華的亮點有了。
大學再讀,她發現原句來自《病隙碎筆》,史鐵生講愛情,還有前半句,“你要愛就要像一個癡情的戀人那樣去愛,像一個忘死的夢者那樣去愛……”被摘出的後半句現在仍然風靡互聯網,被應用到任何場景,就像一支強心劑,讀一下就能“重振熱情的生活”。
但楊悅現在發現做不到了,她無數次試圖用話語激勵自己,這支強心劑卻太過短暫,甚至像一種精神麻醉。她不想再通過文學去認識世界,回到現實,去感受切實的生活,即便殘酷,如仍然找不到的工作,但至少真實。她想了想,“我也未必懂史鐵生,只是在用他解釋我自己。”
但不論如何解釋,生活都要繼續。餘帆仍然在搬運史鐵生的其他語錄,他的目標是商業化。這種金句爆款視頻的粉絲轉化率較低,大多人看過一樂就過了,去商品櫥窗裏買書的更少,目前《我與地壇》和《務虛筆記》賣得算比較好,一共賣出了10本。餘帆計劃後面兩年繼續參加電商賽,比拼數據,因此會繼續做這個賬號,“慢慢來,能做大的。”
©餘帆
張升也想繼續經營讀書博主的賬號,但互聯網看到什麼就做什麼,至於商業化,太久的事情他不考慮。他也不會一直做騎手,最多到明年,父母希望他考公,有穩定的工作,他還是想“創造”點什麼,至於做什麼,那不是現在考慮的事情。他告訴我,“這叫活在當下。”
今天扮演精神支柱的是史鐵生,明天又會是什麼呢?年輕人是主動又被動地加入這場被塑造的時尚嗎?時代癥結又在哪裏?解璽璋沉默半晌,告訴我:“這個問題不是我能回答的,歷史走到今天這一步,是如何造成的呢?我也不知道。”
但不論如何,解璽璋理解這種困境,“大家總要吸收一些力量支撐自己的人生向前走,不能停滯對吧?”
(來源:騰訊新聞)
◦ 應對方要求,餘帆、昭玉、程遇、楊悅、張升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