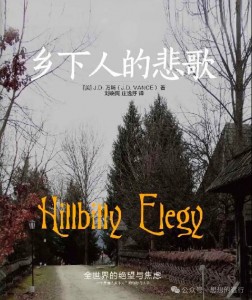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JD萬斯的成名,來源於他的書《Hillbilly Elegy》,中文譯成《鄉下人的悲歌》或《絕望者之歌-一個美國白人家族的悲劇與重生》。2013年他憑着這本書給他帶來的名氣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今年又被川普選作副總統候選人。這本書記述了他在鐵鏽帶成長時的艱辛故事和家庭心酸,與那時比起來,他這幾年他可以說是時來運轉,好運連綿。
這本書寫得相當好,文筆流暢,能讓人“一氣呵成”讀完。故事本身雖然也不難想象,窮白人或者說“白垃圾”的生活就那個樣子,但人們還是願意瞭解更多細節。句子有時很長,但是連貫易懂,我覺得甚至有點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的感覺,當然後者是不斷在路上行走,從東部到西部再回頭,而萬斯的窮白人就停留在家鄉周圍,對世界的變化幾乎無知,只是在夫妻無休止的爭吵,生孩子,嗑藥,這樣的事情上苟活着。
讀這本書的時候你可以看到萬斯的真誠,對自己族羣的困境更多是自省。雖然對同胞有很多看法,但對自己人的剖析再犀利也很難說是偏見,我看不到過去幾年裏他成爲極端右派之後的各種極端的對其它人羣的偏見。從家鄉那裏誤打誤撞進了耶魯,這一段經歷是典型的中國人所說的鳳凰男經歷,從鳳凰男如何變成極端右派,對沒有孩子的人大肆抨擊,成爲極右派的急先鋒,這段比較複雜,我的看法是,從這本書中,你可以看到他對窮白人的生活方式並不認同,也不認爲全球化是讓他們陷入貧困的必然原因,也因此他幾年前還完全不認同川普的言論,說他本質上就是個“壞人”(Bad man),“美國希特勒”,但是,萬斯是無法擺脫他的根的,就像他在書中所說,“你可以逃離肯塔基山區,但肯塔基山區不能離開你”。雖然萬斯經過自己的努力和命運的恩賜,甚至是美國及美國教育制度的愛心(可以說,如果不是照顧他的窮困背景,按照他的學業成績,上不了耶魯,而能進耶魯也確實是無心之果。)既然擺脫不了故鄉的窮白人思維,不如先認同吧,而且要雙倍(double down)。讀者在讀了我下面更多的介紹會更清楚。
萬斯的家庭,他願意追溯到的,就是肯塔基東北部的山區。那裏的人大都來自於愛爾蘭北部的蘇格蘭-愛爾蘭地區,這是美國鄉下人的主力。我在寫關於《蘇格蘭啓蒙運動》的一系列文章中着重談到了他們,他們在英國的時候,就具有極大的反英王壓迫的鬥志,非常熱愛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不少嚴重問題:落後和保守的觀念,其中有些人極端散漫懶惰。英國文豪塞繆爾·約翰遜曾提到,他有一次在那裏看到女人在田裏勞動,男人坐在石堆旁發呆,當他問到爲什麼是這樣的時候,那個男人的媽媽說,男人不能做這些事,他們有更重要的事,但更重要的事無非就是酗酒以及幫助領主打仗。旁人這樣說起他們來,是政治不正確,比如希拉里說他們deplorable,可能就是她沒有勝選的原因。但是萬斯自己說的也差不多:
在美國這個種族意識很強的社會中,我們的分類往往侷限於人們的膚色——黑人、亞洲人和白種人,我們常說白種人有特權(white privilege)。但想了解我們的話,這個分類是不夠的。我們雖是白人,但不同於東北部信奉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白人(WASP)。我是蘇格蘭-愛爾蘭人後裔(Scots-Irish descent)中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數百萬白人工人階級的一員。對這個人羣而言,貧窮是傳統——他們的祖先當年在南方當奴工,然後當佃農和煤礦工人,在較近的年代裏又當機械工和工廠工人。在美國人的稱呼中,他們是鄉下人(hillbilliy)、紅脖子(redneck),或者是白垃圾(white trash)。他們是我的鄰居、朋友和家人。
這些人爲什麼與東北部的人不一樣呢,實際上是繼承了他們在英國時的階級區別。雖然蘇格蘭啓蒙運動很爲保守派所稱道,但啓蒙了的應該還是上層精英,包括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那些人。下層人民無非是在啓蒙之後的環境中生存,與其說受到啓蒙運動啓發,不如說受到啓蒙運動的衝擊,而其中的一些,並不適應,於是背井離鄉來到美國。那些受到啓蒙運動影響成爲美國建國之父以及建國之後的棟樑,大多數還是早期來自英國的那些人,包括五月花號那些尋找宗教自由的人。如果不是因爲美洲的存在,蘇格蘭-愛爾蘭人也不會來,只能在蘇格蘭-愛爾蘭地方苟活下去,饑荒會餓死他們,就如沒來的那些人一樣。但來到美洲的很多,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成爲國家的中堅力量,另一部分沒有本領,成爲農民和打工族。有些後來去西部開拓,而最沒有進取心的就是萬斯家鄉的這些白人。他們的能動性,甚至不如黑人,因爲黑人還願意到城裏工作,有一定的能動性和流動性,但萬斯家的這些白人是絕對想不到或者不想要這樣做的,他說:
一位觀察者曾記錄道:“走遍美國各地,蘇格蘭-愛爾蘭裔美國人一直令我感到震驚。他們是美國最爲持久穩固、變化最少的亞文化羣。當幾乎到處都是對傳統的全盤摒棄時,他們的家庭結構、宗教與政治,還有社會生活仍然保持不變。”
很顯然,這樣不思變化的族羣必然是保守派。這些人,按中國的老話來說就是窮山惡水出的刁民,當然刁民也有自己的“美德”,比如忠誠、不要命、好面子,對家庭和國家的狂熱奉獻。
但對我們外人來說,我想提醒記住萬斯的這句話:
我們也有許多不好的特性。我們不喜歡外來者或者是與我們不一樣的人,不管不一樣的是樣貌、行爲或是說話的方式,而說話方式尤爲重要。想要理解我的故事,你首先必須得了解,我骨子裏是一名蘇格蘭-愛爾蘭“鄉下人”。
從這句話,我並不能推出他們有種族歧視的傾向,但也不能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美好,鄉下人或紅脖子對移民完全沒有偏見。
關於他們的好面子,有點像中國人,萬斯說他們是不願外人看到自己惡劣的一面,在外面是不能說家裏的醜事的,但很多家庭都爭吵不休,常常暴力。而且,除非萬不得已,不付諸法律,而是自行解決,常常就是拳頭。
他們覺得這個世界威脅他們的生存,上升的渠道跟他們全無關係,他們不知道有獎學金,精英學校絕不會錄取他們,萬斯碰巧被耶魯大學錄取,他爸爸懷疑他是否說自己是少數族裔。
因此,在偏見中他們異常悲觀。萬斯說:
令人喫驚的是,據調查顯示,白人工人階級是美國最悲觀的羣體。拉美裔移民當中許多人面臨着難以想象的貧窮,黑人的物質生活前景也落後於這些白人,但我們比他們都悲觀。雖然很多羣體明顯比我們更爲貧困。這種現象就說明,肯定是金錢之外的某些地方出了問題。確實如此,我們從未如此地脫離社會,而我們還將這種孤立感傳給我們的孩子。我們的信仰也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地圍繞教堂,更多地依賴情緒化的修辭,而不是那種可以幫助孩子進步的必要社會支持。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退出了體力勞動大軍,不爲更好的機會而搬遷。我們文化中的某些特性帶來了特有的男性危機,這種危機使得我們的男性形成了某些劣根性,難以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
至少在出書的時候,萬斯並沒有怨社會,而是誠懇地在自己族裔的身上找問題。他說:
當我提及我們社區的困境時,總能聽到一種解釋:“J.D.,白人工人階級的前景惡化了。他們的離婚率在增加,結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都是是因爲他們沒有什麼經濟機會。只要他們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們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會相應地好轉。” 我自己年輕時也曾這樣認爲,我拼命想相信這種觀點。它聽起來很有道理。沒有工作會造成很大壓力,而沒有足夠生存的錢會更有壓力。隨着中西部的製造業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階級不僅失去了自己經濟上的安全感,還隨之失去了穩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但後來,我的經歷告訴我:這種關於經濟上不安全感的說法有其偏頗之處。
幾年之前,在我進入耶魯法學院前的那個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職工作,以便攢點錢。我在家附近一家中等規模的地磚分銷公司打工。我的工作就是把地磚搬到貨板上。這份工作雖不輕鬆,但一小時能掙13美元,我正需要用錢。就接受了這份工作,並儘量多輪班和加班。一小時13美元對我家鄉的單身漢來說不算是小錢了——一間不錯的公寓的月租也才500美元左右,而且地磚公司還有穩定的加薪。幹過幾年的員工一小時至少能掙16美元,也就是年收入32000美元——這比哪怕一個家庭的貧困線都高出不少。雖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對穩定的環境,但管理者發現很難找到長期員工。在我離開之前,倉庫共有3名員工,雖然我當時只有26歲,卻比其他員工年長許多。其中有一名員工叫鮑勃(Bob,化名),他在我之前幾個月剛剛到這個倉庫工作。他當時19歲,有一個懷孕的女友。經理非常體貼地給了他女友一份接聽電話的行政工作。但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現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兩天就要逃一天班,而且從不預先通知,而他則是長期遲到。不僅如此,他每天還要上3~4次廁所,一去就是半小時以上。最終,鮑勃也被解僱了。被解僱時,他對着經理怒斥道:“你怎麼能這樣對我?你不知道我有一個懷孕的女友嗎?”像他這樣的還不止一個,我在地磚倉庫工作的短短時間裏,至少還有兩個人也丟掉了工作,其中還有鮑勃的表哥。
這裏萬斯對他們的散漫懶惰有具體的描述,這就是文化。曹德旺的福耀公司最近因爲僱傭政策出了事,大概是給員工的工資福利違背了美國的政策。我們的內卷文化確實過分,但美國鄉下白人的這種散漫是另一種極端。不僅是下層白人,白領也沒有競爭力,比如臺積電在亞利桑那的場子就遲遲開不了工。也是如此。
那時,萬斯也沒有加入極端的右翼來攻擊移民和全球化,他說:
雖然我在這本書裏面關注的是我認識的這類人,即阿巴拉契亞地區的白人工人階級,但我並不是說我們這類人比其他人更值得同情。我寫這本書的初衷並不是要說明白人比黑人或其他人種有更多值得抱怨的地方。我希望這本書的讀者能摘下種族的有色眼鏡,來從中感受階層和家庭是如何對窮人造成影響的。對許多分析家來說,(尤其是華人川粉),一聽到“喫福利的”,腦海裏就會浮現出靠失業救濟金過活的懶惰的黑人母親形象。這本書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我認識的一些“喫福利的”——有些還就是我的鄰居,都是白人。
我當年在地磚倉庫所看到的問題比宏觀經濟趨勢和政策有更深的層面。太多的年輕人對努力工作並不感冒,好的工作崗位總是找不到人。一個年輕人有着各種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養未來的妻子還有即將出生的孩子,他卻願意丟掉一份有着很好醫療保險的不錯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當丟掉自己工作的時候,還認爲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種主觀能動作用——他認爲自己對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總是想要責怪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這種現象與現代美國的經濟格局格格不入。
有一次我問一個相識他的爸爸做什麼工作時,他說他沒有工作,而且以此爲榮。
我們往往總是美化自身好的方面,又對不好的方面視而不見。這就是爲什麼阿巴拉契亞地區的人們會強烈反對一篇關於該地區最貧窮的人的坦誠報道。這也是爲什麼我崇拜我們家族的男人的原因,我們在乎榮譽,也是我爲什麼在18歲之前假裝全世界都有問題,而我們自己卻沒有。真相是冷酷的,但對於鄉下人來說,那些最冷酷的真相,必須由他們自己來說。毫無疑問,我們那裏滿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但那裏也滿是癮君子。此外,我們這裏的人,他有時間來生出八個孩子,卻沒時間來供養他們。毫無疑問,這裏是美麗的,但它的美麗卻被遍佈鄉村的環境廢物和垃圾所掩蓋。這裏的人們勤勞,不過當然不包括那些領着食品券卻對踏實工作無動於衷的人。正如我們家族的男人一樣,這裏是充滿了矛盾。
我並不想說這些窮人就是懶惰,但他們的文化確實有問題,就是與現代經濟格格不入,並不是像川普和川粉所叫囂的,都是因爲移民。這也不是我說的,而是來源於他們的副總統候選人萬斯先生的原話。我也不想再攻擊萬斯關於生孩子多的人應該有更多話語權的話,他在這裏對孩子多,“有娘養無娘教”的情況已經給予否定。他自己的媽媽有三任丈夫,他是第二任所生。還有無數的男朋友,萬斯記錄下來的就有四個。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他開始忘掉這一切,開始攻擊沒有孩子的人們。他書中的話和他後來的話對比起來簡直就是笑話。但沒辦法,他現在想開了,鳳凰男好不容易可以出人頭地,離世界最有權力的寶座只是一步之遙,當然要騙窮白人的選票,讓極右派開心,必須睜大眼說瞎話。
對了,前幾天,萬斯在集會上開了個玩笑,大概是說民主黨總是說他們種族歧視,他喜歡喝無糖山露飲料(Diet Mountain Dew)也可能被人稱爲有種族歧視傾向。結果沒幾個人笑,場面有些尷尬。這個典故也有出處。萬斯說:
現在肆虐家鄉的藥物成癮自從我媽媽成年後就一直折磨着她。而沒有毒品的時候,山露汽水口腔病在那裏尤甚,每個人,包括孩子,都一口爛牙,因爲高糖的山露汽水。
當記者報道這個事情的時候,本地人大怒,認爲這是污衊。社會學家卡羅爾·A.馬克斯托勒姆、希拉·K.馬歇爾)和羅賓·J.泰倫在2000年12月份的一篇論文中指出,鄉下人很早就學會用逃避的方式來處理令人不安的真相,或者是假裝現實比真相要好。這種傾向固然能帶來心理學上的柔韌性,但同時也加大了阿巴拉契亞地區的人們正視自身的難度。
對於奧巴馬,萬斯的家鄉人聽從川普的話,認爲他是穆斯林,或者不是在美國出生的,不過萬斯不這樣,他覺得這都是家鄉人的偏見。他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爲奧巴馬與他們不同:
我現在的一些朋友認爲是種族主義造成了對這位總統的偏見。但很多家鄉人排斥“外人”奧巴馬的情緒並非出於膚色原因,而是別的。想想我高中同學中沒有一個能上常春藤學校,而奧巴馬上過兩所常春藤名校,都表現優異。他聰明、富有,說話像個憲法學教授——事實上他就是個憲法教授。他身上沒有一點像我小時候崇敬的那些人:奧巴馬口齒清晰、聲音動人、說話不偏不倚,不像我們這地方的人;奧巴馬的履歷完美得嚇人;他在芝加哥這個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生活;他舉手投足都透着一股自信,因爲他深知現代美國任人唯賢的體制就是爲他打造的。當然,奧巴馬也曾憑藉他自己的力量克服過我們許多人經歷過的逆境,但那是在人們認識他很久以前。我們認爲他就是與我們不一樣的精英,因此他們相信對奧巴馬的任何謠言。
寫書的時候,萬斯還很真誠,他說:
我家的情況,委婉一點的說法是,我和父母間的“關係比較複雜”,我媽接近整整一生都在和毒癮做鬥爭。把我帶大的外祖父母連高中都沒畢業,而我的整個大家庭裏上過大學的人也寥寥無幾。各種各樣的統計都會顯示,像我這樣的孩子前景黯淡——我們當中幸運的那些,可以不用淪落到接受社會救濟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則有可能會死於過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鄉小鎮僅僅去年就有幾十人因此死去。我曾是那些前景黯淡的孩子之一。我差點因爲學習太差而從高中輟學,也差點屈服於身邊每個人都有的那種憤怒與怨恨。現在,人們看到我時,看到我的工作和常春藤名校的畢業證書時,都會以爲我是什麼天才,認爲只有特別出衆的人才會走到我今天這一步。儘管我對這些人毫無惡意,但恕我直言,這種理論其實是一派胡言。就算我有什麼天分,如果不是得到了許多慈愛的人的拯救,這些天分也會白白浪費了。
尤其是,那時候他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加入對移民憤怒和仇恨的隊伍。他感謝很多人,包括他在耶魯的老師、鼓勵他寫書的華人教授蔡美兒和他那“聰明、溫和、苗條,與家鄉人不同,善於溝通而不是吵架的印度妻子。
來源:白大偉 “思想的遠行”公衆號
作者投稿